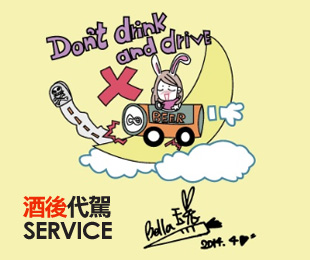гҖҠиҮәзҒЈй…’駕йҳІеҲ¶зӨҫжңғй—ңжҮ·еҚ”жңғйҖҡиЁҠгҖӢ第е…ӯеҚҒдәҢжңҹ 2025.06
иҮәзҒЈй…’駕йҳІеҲ¶
зӨҫжңғй—ңжҮ·еҚ”жңғйҖҡиЁҠ
第е…ӯеҚҒдәҢжңҹ
2025.06

|
|
иҮәзҒЈй…’駕йҳІеҲ¶зӨҫжңғй—ңжҮ·еҚ”жңғ
иҮәзҒЈй…’駕йҳІеҲ¶зӨҫжңғй—ңжҮ·еҚ”жңғиҮӘ2013е№ҙ12жңҲ07ж—ҘжҲҗз«ӢиҮід»ҠйӮҒе…Ҙ第12е№ҙгҖӮ
жң¬жңғзөҗеҗҲзӨҫжңғеҠӣйҮҸпјҢд»ҘNGOж°ёзәҢ經зҮҹжЁЎејҸжҲҗз«ӢпјҢиҮҙеҠӣ於酒駕йҳІеҲ¶е®Је°ҺгҖҒж•Ұдҝғ酒駕дҝ®жі•гҖҒзӣЈзқЈдёӯеӨ®еҲ°зёЈеёӮ酒駕йҳІеҲ¶ж”ҝзӯ–ж–ҪиЎҢжҲҗж•ҲгҖҒ酒駕еһӢж…Ӣд№ӢиӘҝжҹҘеҲҶжһҗиҲҮз ”з©¶гҖҒеҚ”еҠ©й…’駕еҸ—е®іиҖ…иҲҮ家еұ¬д№Ӣжі•еҫӢй—ңжҮ·дәӢй …зӯүпјҢз©ҚжҘөйҷҚдҪҺ酒駕еҚұе®іпјҢзӮәеңӢдәәдәӨйҖҡе®үе…ЁиҲҮе®үе®ҡзӨҫжңғзӣЎдёҖд»ҪеҝғеҠӣгҖӮ

жңҖж–°ж¶ҲжҒҜ
иЎҢеӢ•и¶іи·Ў-
酒駕йҳІеҲ¶е°ҲйЎҢе®Је°ҺиӘІзЁӢ
е…ЁеңӢе·Ўиҝҙ
зӮәиҗҪеҜҰ酒駕йҳІеҲ¶гҖҒеј·еҢ–дәӨйҖҡе®үе…ЁиҲҮжҺЁеӢ•й…’зІҫеҒҘеә·ж•ҷиӮІпјҢжң¬жңғжҺЁеӢ•гҖҢ酒駕йҳІеҲ¶е°ҲйЎҢе®Је°ҺиӘІзЁӢе·ЎиҝҙгҖҚиЁҲз•«пјҢйӮҖи«Ӣе…ЁеңӢеҗ„еӨ§йҶ«йҷўеӨ–еӮ·гҖҒзІҫзҘһ科йҶ«её«еҸҠе°ҲжҘӯи¬ӣеё«зө„жҲҗе®Ји¬ӣеңҳйҡҠпјҢж·ұе…Ҙе…ЁеңӢзӣЈзҗҶж©ҹй—ңгҖҒеҸёжі•зі»зөұгҖҒе°‘е№ҙи§Җиӯ·жүҖгҖҒзҹҜжӯЈж©ҹж§ӢиҲҮеңӢи»ҚйғЁйҡҠзӯүйҖІиЎҢе®Је°ҺпјҢжңҖйҒ жӣҫиөҙз¶ еі¶пјҢз”ҡиҮіеүҚеҫҖж®Ҝиӯ°йӨЁиҫҰзҗҶйҳІй…’駕з”ҹжӯ»ж•ҷиӮІи¬ӣзҝ’пјҢйҮқе°ҚдёҚеҗҢж—ҸзҫӨиҲҮ酒駕й«ҳйўЁйҡӘиҖ…пјҢиҰҸеҠғиӘІзЁӢйҖІиЎҢе®Је°ҺгҖӮ
иӘІзЁӢе…§е®№иһҚеҗҲй…’зІҫе°Қиә«еҝғеҒҘеә·еҪұйҹҝгҖҒйҶ«зҷӮиЎӣж•ҷгҖҒ酒駕еӨ–еӮ·гҖҒ酒駕法еҫӢиҲҮиЎҢзӮәеҝғзҗҶзӯүе°ҲжҘӯйқўеҗ‘пјҢдёҰйҖҸйҒҺ酒駕еҸ—е®іиҖ…зҙҖйҢ„зүҮгҖҒ酒駕дәӢж•…еҪұзүҮгҖҒ酒駕模擬зңјйҸЎй«”й©—гҖҒй…’зІҫдёҚиҖҗз—ҮиҮӘжҲ‘жӘўжё¬зӯүжҙ»еӢ•ж•ҷеӯёпјҢеўһж·»иӘІзЁӢиұҗеҜҢгҖҒдә’еӢ•иҲҮеӨҡжЁЈжҖ§пјҢжҜҸе№ҙиҫҰзҗҶи¶…йҒҺ40е ҙж¬ЎпјҢиҮід»Ҡе…ЁеңӢзҙҜиЁҲи¶…йҒҺ400е ҙж¬ЎпјҢеҪұйҹҝж•ёиҗ¬еҗҚеңӢдәәпјҢдјҒзӣји—үз”ұиҒҶиҒҪиӘІзЁӢзҡ„еӯёе“Ўж“”д»»е®Је°ҺзЁ®еӯҗпјҢж“ҙж•ЈиҮіе…ЁеңӢеҗ„и§’иҗҪгҖӮ

|
|
ж Ўең’ж·ұиҖ•иЎҢеӢ•и¶іи·Ў-
е…ЁеңӢй«ҳдёӯиҒ·иҫҜи«–жҜ”иіҪ
酒駕йҳІеҲ¶е®Је°Һжҙ»еӢ•
йҳІеҲ¶й…’駕еӣӣеҹәзҹіпјҡгҖҢй җйҳІгҖҒиҷ•зҪ°гҖҒжІ»зҷӮгҖҒж•ҷиӮІгҖҚпјҢе…¶дёӯд№ӢгҖҢж•ҷиӮІгҖҚпјҢд№ғжҳҜжңҖж №жң¬зҡ„й•·д№…д№ӢйҒ“пјҢе”ҜжңүеңӢдәәзҷјиҮӘе…§еҝғжҳҺзҷҪ酒駕害дәәе®іе·ұд№ӢеҚұйҡӘжҖ§пјҢйҖІиҖҢжӢ’зө•й…’駕пјҢз”ҡиҮіеҪұйҹҝе‘ЁйҒӯиҰӘеҸӢпјҢе…ұеҗҢзҮҹйҖ жӢ’зө•й…’駕зҡ„зӨҫжңғж°ӣеңҚпјҢж–№иғҪзңҹжӯЈиҗҪеҜҰйҳІеҲ¶зӣ®жЁҷгҖӮ
йқ’е°‘е№ҙжӯЈиҷ•ж–јеғ№еҖји§ҖйӨҠжҲҗйҡҺж®өпјҢеҗҢжҷӮеҚіе°ҮйӮҒе…ҘеҸҜеҗҲжі•еҸ–еҫ—駕照зҡ„е№ҙйҪЎпјҢзӮәдәӨйҖҡе®үе…Ёж•ҷиӮІжңҖй—ңйҚөжҷӮжңҹгҖӮиӢҘиғҪж–јеңӢгҖҒй«ҳдёӯж•ҷиӮІйҡҺж®өжңүж•Ҳж•ҷе°ҺжӯЈзўәдәӨйҖҡе®үе…Ёи§ҖеҝөпјҢдёҚеғ…иғҪйҷҚдҪҺжңӘдҫҶеҫһдәӢеҚұйҡӘ駕й§ӣиЎҢзӮәд№ӢйўЁйҡӘпјҢд№ҹжңүеҠ©ж–је»әз«Ӣй•·йҒ зҡ„е…¬е…ұе®үе…Ёж„ҸиӯҳгҖӮ
жңүй‘‘ж–јжӯӨпјҢжң¬жңғиҮӘ112е№ҙиө·пјҢе•ҹеӢ•д»Ҙйқ’е°‘е№ҙзӮәж ёеҝғд№ӢгҖҢе…ЁеңӢй«ҳдёӯиҒ·иҫҜи«–жҜ”иіҪ 酒駕йҳІеҲ¶е®Је°Һжҙ»еӢ•гҖҚпјҢи—үз”ұй«ҳзҙҡдёӯеӯёиҫҜи«–зӨҫеңҳжҙ»еӢ•е°Ү酒駕йҳІеҲ¶иӯ°йЎҢж·ұиҖ•ж Ўең’пјҢйҖҸйҒҺеҸғиіҪйҒёжүӢйҪҠиҒҡзҡ„е ҙеҗҲпјҢеҗ‘йқ’е№ҙеӯёеӯҗе®Је°Һ酒駕йҳІеҲ¶иҲҮй…’зІҫеҒҘеә·дё»йЎҢпјҢдёҰеҠ е…Ҙдә’еӢ•еҜҰй©—иҲҮйқ’е°‘е№ҙйҖІиЎҢе°Қи©ұпјҢи®“гҖҢдёҚ酒駕гҖҚжҲҗзӮәиҮӘжҲ‘еғ№еҖјиҲҮиІ¬д»»гҖӮ

й…’жқҜиЈЎзҡ„и¬Җж®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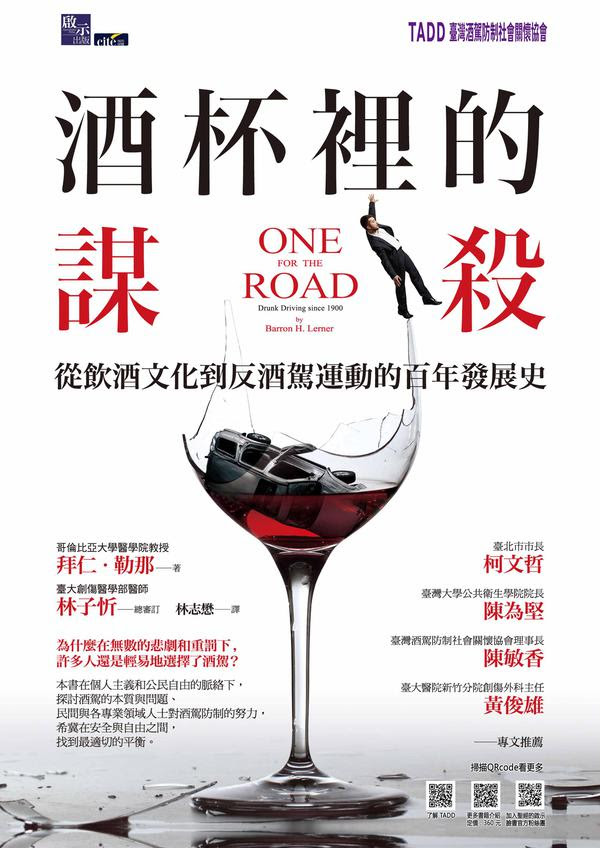
йҒӢеӢ•зҡ„жҲҗзҶҹиҲҮеҲҶиЈӮ
еӣ 酒駕иҖҢиө·зҡ„йҒ“еҫ·зҫ©жҶӨеҰӮдҪ•ж“әеёғгҖҢдәӢеҜҰгҖҚпјҢеј•иө·дәҶеҸҰеӨ–е…©дҪҚз ”з©¶дәәе“Ўзҡ„иҲҲи¶ЈпјҢйҖҷе…©дҪҚеҚ“然жңүжҲҗзҡ„зӨҫжңғеӯёе®¶жҳҜеҠ е·һеӨ§еӯёиҒ–ең°зүҷе“ҘеҲҶж Ўзҡ„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пјҢд»ҘеҸҠеҺҹдҫҶеңЁзҙҗзҙ„е·һз«ӢеӨ§еӯёж°ҙзүӣеҹҺеҲҶж ЎгҖҒеҫҢдҫҶеҲ°ж–°еўЁиҘҝе“ҘеӨ§еӯёзҡ„зҫ…ж–ҜпјҲH. Laurence RossпјүгҖӮдёүеҚҒе№ҙеҫҢпјҢд»–еҖ‘зҡ„з ”з©¶жҲҗжһңе·§еҰҷиӯүжҳҺпјҢй…’й§•з ”з©¶иҲҮж”ҝзӯ–зҡ„еҹәжң¬дҝЎжўқжңүжҷӮжҳҜе»әз«ӢеңЁйҢҜиӘӨзҡ„еүҚжҸҗдёҠгҖӮ
1980е№ҙд»Јзҡ„зӨҫжңғеӯёијӘеҲ°жүҖи¬Ӯзҡ„гҖҢзӨҫжңғе»әж§Ӣи«–гҖҚпјҲsocial constructionismпјү當йҒ“гҖӮйҖҷдёҖжҙҫиӘҚзӮәпјҢдәӢеҜҰжҳҜеңЁи§ҖеҜҹгҖҒз«Ӣе ҙпјҢд»ҘеҸҠе°ҚжӯӨдәҢиҖ…жңүжүҖз ”з©¶зҡ„еҖӢдәәжүҖеҫ—д№Ӣзөҗи«–пјҢдёүиҖ…зҡ„иӨҮйӣңж··еҗҲдёӯжҲҗеҪўгҖӮжӯӨдёҖзҗҶи«–жңҖжҘөз«Ҝзҡ„ж”ҜжҢҒиҖ…дё»ејөпјҢжІ’жңүе®ўи§ҖеҜҰеңЁйҖҷзЁ®жқұиҘҝпјҢеҸӘжңүе°Қе®ўи§ҖеҜҰеңЁзҡ„дёҚеҗҢе»әж§ӢгҖӮдҪҶеӨ§еӨҡж•ёз ”з©¶жӯӨдёҖй ҳеҹҹзҡ„зӨҫжңғеӯёиҖ…дёҰжІ’жңүйӮЈйәјеҒҸгҖӮд»–еҖ‘еҖ’жҳҜиӘҚзӮәпјҢз ”з©¶йӮЈдәӣжүҖи¬Ӯзҡ„гҖҢдәӢеҜҰгҖҚиіҙд»ҘзӮәж”Ҝж’җзҡ„еҒҮиЁӯпјҢе’ҢиіҮж–ҷжң¬иә«дёҖжЁЈйҮҚиҰҒпјҢз”ҡжҲ–жӣҙзӮәйҮҚиҰҒгҖӮ
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жҳҜеҜҰйҡӣжҮүз”ЁйҖҷзЁ®жҖқиҖғеҪўејҸзҡ„еӨ§её«гҖӮд»–жңҖеҲқзҡ„з ”з©¶иҲҲи¶ЈжҳҜзҰҒй…’д»ӨгҖӮд»–зҡ„第дёҖжң¬жӣёгҖҠиұЎеҫөжҖ§зҡ„иҒ–жҲ°пјҡиә«еҲҶж”ҝжІ»иҲҮзҫҺеңӢзҰҒй…’йҒӢеӢ•гҖӢеҮәзүҲж–ј1963е№ҙпјҢжӣёдёӯдё»ејөпјҡзҰҒй…’д»ӨиҲҮе…¶иӘӘжҳҜеңЁиҷ•зҗҶй…’зІҫиӯ°йЎҢпјҢеҖ’дёҚеҰӮиӘӘжҳҜжҹҗдёҖзҫӨзҫҺеңӢдәәжғіиҰҒйҒӢз”ЁйҒ“еҫ·ж”№йқ©пјҢдҫҶдҝқдҪҸиҮӘиә«еңЁи®ҠеӢ•зӨҫжңғдёӯзҡ„иә«еҲҶең°дҪҚгҖӮ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и·Ёе…Ҙ酒駕й ҳеҹҹзҡ„еҘ‘ж©ҹпјҢжҳҜд»–зҚІйӮҖйҮқе°ҚиҒ–ең°зүҷе“ҘйғЎжі•йҷўзі»зөұзҡ„酒駕еҜҰйҡӣеҲӨдҫӢйҖІиЎҢз ”з©¶гҖӮд»–жҳҜеӣ зӮәе°ҲзІҫж–јй…’зІҫжҲҗзҷ®з—ҮиҖҢиў«йҒёдёӯпјҢеҲ°жң«дәҶпјҢд»–е°ҮеҶҚж¬ЎиҒҡз„Ұж–јйҒ“еҫ·дё»зҫ©зҡ„иӯ°йЎҢдёҠгҖӮ
з”ұж–јд»–зҡ„зөҗи«–жҳҜ酒駕宣еҲӨзҡ„зӣёй—ңдәәеЈ«е…ЁйғҪе…ұжңүзӣёеҗҢзҡ„еҒҮиЁӯпјҢе°ҚзӨҫжңғе»әж§Ӣи¶ҠдҫҶи¶Ҡж„ҹиҲҲи¶Јзҡ„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пјҢе•ҸдәҶдёҖеҖӢд»ӨдәәиҖізӣ®дёҖж–°зҡ„е•ҸйЎҢпјҡеңЁй…’зІҫеҪұйҹҝдёӢ駕й§ӣжұҪи»ҠпјҢеҲ°еә•жҳҜзӮәд»ҖйәјжҲҗдәҶе…¬е…ұе•ҸйЎҢпјҹгҖҗиЁ»4гҖ‘йҖҷжўқжҺўиЁҺжҖқи·ҜжңҖзөӮе°Үеј•еҮәд»–зҡ„酒駕еӨ§дҪңгҖҠе…¬е…ұе•ҸйЎҢзҡ„ж–ҮеҢ–пјҡй…’еҫҢ駕й§ӣиҲҮиұЎеҫө秩еәҸгҖӢпјҲ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: Drinking-Driving and the Symbolic OrderпјүпјҢеҮәзүҲж–ј1981е№ҙгҖӮйҖЈжӣёеҗҚйғҪйЎҜзӨәеҮә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е°Қз”ЁиӘһзҡ„謹ж…ҺжіЁж„ҸпјҢд»–жҸҗеҲ°й…’еҫҢ駕й§ӣпјҲdrinking drivingпјүдёҖи©һе°Қж–ји©Ій ҳеҹҹз ”з©¶е°ҚиұЎзҡ„жҸҸз№ӘжӣҙзӮәзІҫзўәгҖӮзӣёијғд№ӢдёӢпјҢй…’йҶү駕й§ӣпјҲdrunk drivingпјүдёҖи©һеё¶жңүдёҚиЁҖеҸҜе–»зҡ„иІ йқўж¶өзҫ©пјҢд№ҹж¶өи—Ҹи‘—еҸҜиғҪз”ўз”ҹиӘӨе°Һзҡ„еҒҮиЁӯпјҡ駕й§ӣжүҖйңҖиҰҒйҒҝе…Қзҡ„пјҢж“әжҳҺдәҶе°ұжҳҜгҖҢй…’йҶүгҖҚгҖҗиЁ»5гҖ‘гҖӮ
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зҡ„жӣёиҷ•иҷ•еҸҜиҰӢд»–зӯҶдёӢжүҖзЁұд№ӢгҖҢиҷӣж§ӢгҖҚпјҢд»ҘеҸҠжӣ–жҳ§е’Ңз–‘ж…®жҘӯ經гҖҢ移йҷӨгҖҚгҖҒгҖҢзўәе®ҡ且經жҹҘж ёзҡ„йҖҡи«–иҲҮдәӢеҜҰд№ӢиЎЁиұЎгҖҚгҖӮе…¶дёӯд№ӢдёҖе°ұжҳҜиЎҖдёӯй…’зІҫжҝғеәҰгҖӮзңҫжүҖе‘ЁзҹҘпјҢеҗҢжЁЈзҡ„жҝғеәҰеңЁдёҚеҗҢзҡ„дәәиә«дёҠжңғе°ҺиҮҙдёҚеҗҢзҡ„еӨұиғҪзЁӢеәҰ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—ҘжјёдҫқиіҙиЎҖдёӯй…’зІҫжҝғеәҰдҫҶзўәе®ҡ駕й§ӣжҳҜеҗҰеҸ—й…’зІҫеҪұйҹҝпјҢжҳҜжңғ鬧笑и©ұзҡ„пјҢеӣ е…¶жүҖжё¬йҮҸзҡ„жҳҜгҖҢиЎҖдёӯй…’зІҫгҖҚпјҢиҖҢйқһгҖҢй…’зІҫе°Қ駕й§ӣиғҪеҠӣзҡ„еҪұйҹҝгҖҚ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ӘӘпјҢйҢҜжҠҠгҖҢз”ҹеҢ–зӢҖж…ӢгҖҚ當жҲҗдәҶгҖҢиЎҢзӮәзӢҖж…ӢгҖҚгҖӮ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йҡЁеҚіеқҰиЁҖ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еӣ зӮәйҖҷеҖӢзҗҶз”ұе°ұиҰҒжҚЁжЈ„иЎҖдёӯй…’зІҫжҝғеәҰпјҢдҪҶз”ұжӯӨжүҖеҫ—зҡ„иіҮиЁҠпјҢдёҚз®ЎжҖҺйәјиӘӘпјҢйғҪжҳҜгҖҢжҶ‘з©әиЈҪйҖ зҡ„зҹҘиӯҳгҖҚгҖҗиЁ»6гҖ‘гҖӮ
йӮ„жңүдёҖеҖӢжӣҙеӨ§зҡ„е•ҸйЎҢжҳҜгҖҢиҷӣж§Ӣзҡ„зӣёй—ңжҖ§гҖҚпјҢйҖҷд№ҹжҳҜжҝҹзҲҫжӣјжҸҗеҮәзҡ„и«–й»һгҖӮжҝҹзҲҫжӣјдё»ејөпјҢй…’зІҫиҲҮ駕й§ӣиЎҢзӮәзҡ„з ”з©¶жңүдёҖеҖӢйҢҜиӘӨзҡ„еҒҮиЁӯпјҡдәӢж•…дёӯжңү駕й§ӣжҲ–иЎҢдәәе–қй…’пјҢеҚіеҸҜиӯүжҳҺй…’йҶүжҳҜи»ҠзҰҚиӮҮеӣ гҖӮз•ўз«ҹпјҢ50%д»ҘдёҠзҡ„и»ҠзҰҚдёҰжңӘж¶үеҸҠй…’зІҫпјҢиҖҢжҳҜеӨң間駕й§ӣгҖҒз–ІеӢһгҖҒ駕й§ӣдёҚе°ҲеҝғгҖҒжҝ•ж»‘йҒ“и·ҜгҖҒи¶…йҖҹпјҢжҲ–й‘‘иӯҳдәәе“Ўж №жң¬е°ұжІ’зҷјзҸҫзҡ„е…¶д»–еӣ зҙ гҖӮйҖҷдәӣеӣ зҙ еҫҲеҸҜиғҪд№ҹеңЁжңүдәәйЈІй…’зҡ„жЎҲдҫӢдёӯзҷјжҸ®дҪңз”ЁгҖӮеҸӨж–ҜиҸІзҲҫеҫ·йӮ„иӘӘпјҢеӨ§еӨҡж•ёи»ҠзҰҚиӮҮеӣ зўәеҜҰеҫҲжңүеҸҜиғҪжҳҜеӨҡйҮҚеӣ зҙ 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зӮәд»ҖйәјжҲ‘еҖ‘еҫ—еҒҮе®ҡпјҢеңЁж¶үеҸҠй…’зІҫзҡ„жЎҲдҫӢдёӯпјҢй…’еҫҢ駕й§ӣдәәе°ұжҳҜзҪӘйӯҒзҰҚйҰ–пјҹе•ҸйЎҢеңЁж–јгҖҢзӣёй—ңжҖ§иў«иҪүжҸӣжҲҗеӣ жһңжҖ§гҖҚпјҢеҸҰдёҖдҪҚжү№и©•иҖ…еҗҚд№Ӣжӣ°гҖҢжғЎж„Ҹзҡ„еҒҮиЁӯгҖҚгҖҗиЁ»7гҖ‘гҖӮ
гҖҗиЁ»4гҖ‘Joseph R. Gusfield,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: Drinking-Driving and the Symbolic Order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1), xii.
гҖҗиЁ»5гҖ‘еҮәиҷ•еҗҢеүҚпјҢ79.
гҖҗиЁ»6гҖ‘еҮәиҷ•еҗҢеүҚпјҢ63-66.
гҖҗиЁ»7гҖ‘еҮәиҷ•еҗҢеүҚпјҢ74,Joseph R.Gusfield,“The Control of Drinking-D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: A Period in Transition?" in Michael D. Laurence, John R. Snortum,and Lawrence E. Zimring, eds., Social Control of the Drinking Driver (Chicago: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8), 109-35.
й—ңеҝғ酒駕ж¶ҲжҒҜ
иҝҪи№Ө酒駕新иҒһ
жҚҗж¬ҫйҳІеҲ¶й…’駕